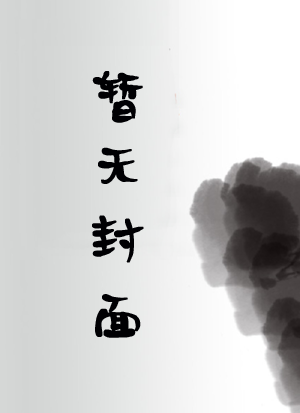王安石默默打開《流民圖》,注視了幾秒鐘,便把《流民圖》遞到韓绛手中,韓绛才看了一眼,冷汗就冒了出來。他張口正欲設辭分辯,不料王安石輕輕搖了搖頭,跪下說道:“陛下,此圖所繪,的确就是外面百姓的慘狀了。”
韓绛絕對沒有想到王安石會一口承認,真的大吃一驚。天子在九重之内,外面是個什麼樣子,還不是大臣們說了算?!現在雖然有報紙了,但是巧言設辭,也并非難事。他實是不知道王安石為何竟要一口承認。若是石越在此,必然也要吃驚的。因為他所學過的曆史書,黨百般抵賴的。
趙顼見王安石承認,真是又驚又怒!“王卿,你、你……”皇帝此時隻是用手指着王安石,卻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王安石微微歎了口氣,沉聲說道:“陛下,臣深負聖恩,萬死不能救其罪。現在既知事事屬實,斷無欺君之理!”
韓绛聽到趙顼和王安石的對話,心裡卻也一樣亂成一團,完全失去了分析後果的能力。
趙顼瞪視王安石良久,又是失望又是焦慮,最後終于把手放下,一**坐在龍椅上,閉着眼睛,緩緩說道:“既是屬實,這幅《流民圖》,就挂在禦書房内。也好讓朕天天記得,朕的子民們現在是什麼樣子!”
王安石心中的灰心,其實比皇帝遠甚,負天下之望三十餘年,一旦執政,數年之内,先是士大夫沸騰,議論紛紛,自己平素所看重的人,似司馬光、範純仁輩,根本不願意與自己合作;好不容易國家财政漸上軌道,各處軍事上也接連取得勝利,卻來了一場大宋開國百餘年沒有的大災!
“陛下,王丞相執政之前,曾經朝百年無事劄子》,内中言道一旦有事,百姓必然不堪,今日之事,實非新法與丞相之錯,而是替百年之沉苛還債呀!還望陛下明察。”韓绛終于理清了思緒,戰戰兢兢的說道。
王安石望了韓绛一眼,他不知道新法到現在為止,已經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,無論他自己怎麼樣想,這一批人卻是肯定要一直打着新法的旗幟,來在政治上争取主動,維護自己的利益,一旦王安石罷相,萬一皇帝變卦,不再變法,這一群人的政治權益,就會立時失去,從這些人的角度來說,是無論如何都要盡力保住他的。王安石卻隻道韓绛是因為他們幾十年的交情,竭力為他掩飾,心裡不由也頗是感動。
“子華……”王安石叫了一聲韓绛的表字,沉默半晌,方對皇帝說道:“陛下,臣并非是為推行新法而向陛下謝罪。大宋國勢,不變法不行,這是陛下也深知的。臣向陛下謝罪,是因為六年來,陛下對臣的知遇之恩,曠古絕今,信臣用臣,而臣的新法,卻沒有辦法應付一場大災,緻使百姓流離失所!”
趙顼見王安石眼中已經滿含淚水,心裡也不由動容。又聽王安石說道:“方才看到桑充國的文章,臣才知道臣身為宰相,器量竟不如桑充國一介布衣,心下真是慚愧萬分。但是臣的本心,可鑒日月,絕對是對大宋、對皇上的赤膽忠心,絕對沒有想過要盤剝百姓來斂财邀寵!”
趙顼微微點頭,這一點上,他倒是絕對相信王安石。
“雖然如此,但是錯了畢竟是錯了,為相五年,卻是今天這樣的局面,臣非但外慚物議,内亦有愧于神明。石子明離阙之時,囑臣數事,備災荒、緩召王韶、不向交趾用兵,臣沒有一件事做到了。石越回京之日,臣若還在相位,實在羞見石郎!因此臣請陛下許臣緻仕!”
“緻仕?!”趙顼和韓绛不由大吃一驚。
“萬萬不可,陛下,介甫,此事萬萬不可!”韓绛這個号稱“傳法沙門”的韓相公,幾乎有點語無倫次了,“陛下,新法不可半途而廢,否則必然前功盡棄!王丞相若罷,新法必然更加艱難呀!”
桑充國的呼籲、鄭俠上《流民圖》、王安石自請緻仕,汴京的政局卻并沒有因此而變得清晰,想要舊黨放棄這千載難逢的機會,實在是有點一廂情願。隻不過也沒有人會料到,局勢反而更加複雜化了。
朝廷與地方的舊黨,平素與王安石不合的大臣,借着《流民圖》的機會,一波一波的要求皇帝罷王安石、廢新法;連一向不幹預朝政的兩宮太後,也天天要向趙顼哭訴,趙顼被這件事情,搞得暈頭轉向。偏偏蔡确這時候,卻做出了一件更加激化矛盾的事情來,他帶着禦史台所屬兵士,一紙行文,将鄭俠捉住,關進了禦史台的牢獄之中。
此事立時在朝堂上掀起軒然大波。
“陛下,臣以為此事或有不妥。”呂惠卿對蔡确的做法,頗有點不以為然。
蘇頌更是直接質問道:“蔡中丞,不知道鄭俠所犯何罪?”
蔡确冷冷的望了二人一眼,根本不屑于回答,隻是冷笑道:“二位大人不會連大宋的律令都不知道吧?”
趙顼此時實在是傷透腦筋了,蔡确也不請旨,直接把鄭俠系獄,結果當天營救的疏章就達到二十多份,他下旨讓蔡确釋放鄭俠,蔡确毫不客氣的頂了回來:“祖宗自有法度,陛下須做不得快意事!”
“鄭俠到底是犯了何事入獄?”趙顼不得不親自開口詢問。
蔡确見皇帝問,這才躬身回答:“回陛下,是擅馬遞之罪!”
“哦?”趙顼沒有明白過來。
“臣聽到陛下說,陛下接銀台司急奏,卻是鄭俠所上《流民圖》,不知确否?”
“正是。”這件事可以說人人皆知。
“臣當時就想,鄭俠一個監安上門,上《流民圖》,如何能得銀台司急奏?”蔡确這麼一說,趙顼才想起來,自己當時的确也奇怪過。
蘇頌等人聽到這裡,卻也已經略略猜到事情的原委了。原來趙顼登基以來,所閱奏章一向有三種方式,一是中書與樞密轉遞的,這是絕大部分;二是如韓琦這樣的元老、石越這樣的親信,可以直接遞達禦幾之前;三則是密報,密報一向不經中書,直接由銀台司遞進,而且絕不敢延遲,而遞交密報,就需要馬遞。想是鄭俠急欲皇帝知道,便不顧後果,兵行險着,竟然假托密急,騙過銀台司把《流民圖》遞了進去,不料卻被蔡确一眼就瞧出破綻來。
果然蔡确把原委一一道來,這是證據确鑿之事,不僅衆臣,連皇帝也啞口無言。宋代的君權,本來就沒有後世的霸道,大臣把皇帝駁得氣結于兇無可奈何的事情,史不絕書,這時候既然被蔡确抓住了把柄,趙顼雖存着息事甯人之心,卻也不能不好言相向:“念在鄭俠是一片忠心,此事不如照章記過便了。”
蔡确冷笑道:“這次若是放過,下次銀台司的密急,就不知道有多少了。陛下要為鄭俠說情,說不得先請罷了臣這個禦史中丞。否則臣既然掌糾繩百官,區區一個監安上門,還不必勞動天子說情。”
趙顼不料碰了好大一個釘子,卻也隻能搖頭苦笑。
呂惠卿卻心裡奇怪,他知道蔡确雖然時不時在皇帝面前表現得甚有風骨,但是凡是重大事情,其實倒多半是希迎皇帝、王安石之意的,這時候為了一個鄭俠而如此大動幹戈,難道是得了王安石的意思?
“不可能,不可能。”呂惠卿心裡搖搖頭,否定了自己的想法,他可以明顯感覺出王安石最近心情頗異于往常,而且對鄭俠并沒有特别懷恨的樣子。
“這個蔡持正,究竟打的什麼主意?”呂惠卿心裡嘀咕着,揣測蔡确的用意。
然而大部分的新黨,就沒有呂惠卿這麼多心腸,韓绛、曾布、李定等人,心中一個勁直呼痛快!“丞相對鄭俠不薄,把他從光州司法參軍調到京師,本來欲加重用,不料他卻對新法全盤反對,不得己安置他為監安上門,誰知此時卻來反噬!”這黨許多人心中的想法,蔡确一定要治鄭俠的罪,不由讓這些人也對蔡确多了一份親近感來。
相比韓绛等人眼中的贊賞,馮京眼中卻不免多出許多疑慮,“那麼蔡大人打算如何落鄭俠?”平素溫和的他,此時卻是用明顯的諷刺語氣問。
蔡确絲毫不以為意,隻向趙顼說道:“臣以為鄭俠當落職,安置一個小縣,交地方看管,以使後來者知戒。”
“這……”趙顼面有難色,如此處置,朝中必有大臣不服。
果然,他話音未落,馮京就憤然說道:“蔡持正未免處置過重了!”
王安國也跳出來反對,慨然說道:“若鄭俠上《流民圖》而遭黜,是朝廷無公理!請陛下三思!”
劉攽、蘇頌、孫固等人,更是同聲反對。
而似曾布、李定等人,卻不免又要一緻支持,隻有韓绛知道皇帝心意,便默不作聲。
呂惠卿見到這種情形,才立時恍然大悟,原來蔡确竟然是想趁機豎立自己在新黨中的領袖地位!他暗暗冷笑,“蔡持正未免操之過急了!”
當下再不遲疑,朗聲說道:“陛下,臣以為鄭俠擅馬遞,自然是有罪,但是他一片忠心,而且便是幾位丞相,都能體諒的,并沒以為鄭俠是在妄言。因此臣以為,有罪雖不可不治,但法理亦不外乎人情。鄭俠本來是光州司法參軍,王丞相曾稱贊其能,不若再放回光州,依然任司法參軍,同時照章記過。一來以示懲戒之意,二來示天下朝廷之寬仁美德。”
他這番話,卻是兩面顧到,打太平拳的意思,舊黨的感受,呂惠卿本來并不太在乎,但他知道皇帝心中此時必然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,隻不過若是完全不給鄭俠一點顔色看,隻怕新黨中人也要視自己為異類了,當下才說出這麼一個辦法。
果然趙顼聽完,立即點頭同意:“呂卿所言有理,便依如此處置便可。”而韓绛、馮京、曾布等人覺得這個方案也可以接受,也就不再出聲反對。
蔡确知道這個方案提出,别人既無異議,自己便也不便再過份堅持,他萬萬料不到自己一腔心皿竟被呂惠卿賣了個乖,低下頭狠狠瞪了呂惠卿一眼,無可奉何的說道:“臣遵旨!”
桑充國既料不到鄭俠會不和自己與晏幾道商量,就假托密報上《流民圖》,也料不到朝廷的公卿們,此時沒有去想怎麼樣救濟災民、恢複生産,反而在争論着如何處置鄭俠的事情。不過他也沒有心思去想這麼多事情,官府雖然也設了粥場,但是卻嚴格控制府庫的存糧,根本無法滿足這麼多災民的生活之需,白水潭的粥場,吸引的災民越來越多,而倉庫中的存糧,卻一日比一日少了,桑充國雖然有心買糧,可在汴京城,上哪裡能一次買到這麼多糧食呢?
在衆多的災民之中穿行,望着那一雙雙充滿了期望與信任的眼神,桑充國實在不敢去想像徹底無糧的那一天。他無意識的想避開那些眼神,便擡起頭來,向左邊看去,卻現王旁正陪着一個老人在災民間穿行。桑充國連忙信步走過去,招呼道:“王兄。”
王旁看見桑充國走過來,低聲對老者說了幾句什麼,這才笑着回道:“長卿,現在情況怎麼樣?”
桑充國皺眉答道:“情況實在很糟,得病的災民越來越多,人手不足,糧食也快沒有了,朝廷再不想辦法,我不知道還能支持幾天。程先生和邵先生幾位,已經想辦法去了。”一邊朝那位老者行了一禮,招呼道:“老丈,這裡禮數不周,還望恕罪。”
那個老者微笑着點點頭,說道:“不必多禮。”卻是公然受了桑充國這一禮。
桑充國不由一怔,須知他畢竟也是名滿天下的人物,一般人便是長者,也不至于見到他連一句客套話都沒有。王旁知他心意,連忙低聲解釋道:“這是家父。”
桑充國随口應道:“原來是令尊大人——”說到這裡,不由一頓,這才反映過來,王旁的父親,不是王安石嗎?!
“你、你是王相公?”桑充國有點失禮的問道。
好在王安石卻是個不太拘禮法的人,當下微微點頭,笑道:“正是某家,久仰桑公子的大名,不料今日才得相見。”
“不敢,不知相公駕到,學生實在失禮了。”桑充國一面說着,一面就要下拜。
王安石連忙止住,說道:“今日野服相見,桑公子不必多禮。”王旁也笑道:“長卿不要太聲張,家父是想來看看白水潭是怎麼樣救濟災民的。”
聽到王旁提到災民,桑充國看了王安石一眼,歎道:“不瞞相公,如若朝廷再不設法,我們這裡,也要無可奈何了。相公是飽學鴻儒,豈不知綠林、赤眉,皆是饑民嗎?”他說的這話,雖然委婉,卻隐隐有責難之意了。
王安石見他初次見面,便如此坦然,不由暗暗稱奇。他自是不知道白水潭學院一向頗為自許,平時裡便是昌王來此,也并不拘禮,因此白水潭學院的人對于公卿,實在是看得太平常不過,而對所謂的尊卑之分,除了君臣父子師生這些之外,比起别處的人來,倒要淡了幾分。
“某豈有不知之理,不過談到救災之法,卻是苦無良策。”王安石搖了搖頭,回道。
桑充國毫不客氣的說道:“相公這樣說,學生不敢苟同。豈能用‘苦無良策’四個字來推卸責任的?若綠林、赤眉賊起,饑民們可不會聽‘苦無良策’四字。”
王安石不由有幾分尴尬,王旁有點擔心的望着父親,若是往常,隻怕王安石早已怒,今日不知為何,脾氣卻格外的好,隻是苦笑道:“那麼桑公子可有救災之策?”
桑充國說完之後,其實也自覺頗有過份,隻是這幾日急火攻心,猛然碰到王安石出現在自己面前,卻不自覺的要嘲諷幾句解氣。這時候見王安石竟是絲毫不以為意,心裡也不由奇怪,暗道:“王安石人稱拗相公,說是脾氣易躁的,怎的傳聞有誤不成?”嘴上卻回道:“學生不過一介布衣,才疏學淺,又知道什麼國家大事?不過這救災之策,自古以來,無非是開倉放糧,使百姓不必流離失所吧。”
王安石聽到這話,不禁啞然失笑。他雖然并不指望桑充國有石越一般的政治才能,但是也沒有料到桑充國原來竟是書生氣這麼重的人。他不由苦笑道:“若是如此簡單,那便好了。似如此大規模的災情,本州本府,再如何開倉放糧,也是不敷所用的。何況重要州府的軍糧,點都不能動。因此一切隻能靠外郡運糧救濟,而運糧所費,更是驚人。因此似這種大災,除非百姓本來殷實,或者早有準備,否則是無法杜絕流民出現的。”說到後面,王安石眼神不由一黯,本來大宋朝是有機會早點準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