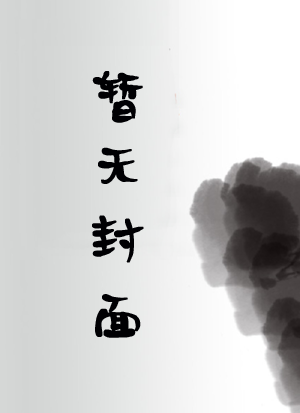時間永遠是最大的。
熙甯十二年的正月,宋朝與西夏,從表面上來看,除了西夏派出使者向宋朝皇帝拜賀正旦以外,雙方都是在為各自的事情毫不相幹地忙碌着。
宋朝在正旦的大典之後,由鴻胪寺卿正式告知遼使,宋朝決定接受了遼國的請求,雙方在對方京城,互設常駐使節,遼國由此成為自高麗國以外獲準在汴京常駐使節的第二個國家。這件小小的事情,實際上傳達了很多的信息:此時的宋朝,正在漸漸變得比以往更加自信,因此也更加開放。
不過,此事由鴻胪寺卿來傳達,卻也意味着對石越主導的官制改革的修訂——當年官制改革之時,規定鴻胪寺負責藩屬、國内少數民族、海外殖民地之事務,而不在朝貢體系之内的國家,如對遼國的外交事務,則歸于禮部。這種設置本是石越試圖打破朝貢外交的一種嘗試,今後的宋朝必将面臨更寬廣的世界,雖然宋朝當之無瑰地處于當時人類文明的頂峰,但是并不意味着其餘的文明隻能有資格葡伏于它的腳下,古老的朝貢體系在石越看來,本就有修正之必要——正視你的競争對手,什麼時候都不會錯。而宋朝本來就視遼國為平等的大國,朝貢體系在這裡已經開了一道縫,因此石越便想巧妙的加以利用。
但是,很快,宋廷就發現了其中的不便:當時與宋朝交往的國家,僅僅隻有遼國是宋朝認為可以平等相處的國家,其餘諸國,連注辇國這樣的天竺強國,都被習慣性的納入了朝貢體系之内,雖然對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屬,但是傳統思維的慣性卻讓宋廷理所當然的将之納入朝貢體系。至于在石越的影響以及對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,被宋朝許多士大夫承認可以與遼國相提并論的近西及泰西諸國(石越《地理初步》之地理概念,大抵西夏以西至中亞,稱為西域,西亞至東羅馬帝國稱為近西,東羅馬帝國以西,則為泰西),卻并未與宋廷發生直接的官方交往,因此自然也被選擇性的忽略了。
在這樣的情況下,禮部主客司就顯得特别的清閑,也特别的刺眼,朝野上下,幾乎一緻同意這是一個冗司,終于,這個機構在熙甯十二年走到了它的盡頭,宋廷首先決定将其事務全部并入鴻胪寺,在一個月後,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。
雖然石越始終堅持認為,國内之蠻夷亦是宋朝之臣民,将其與遼國通聘并屬于一個機構不倫不類,但是他也無法阻止這種曆史的巨大慣性。在宋廷看來,成為國家編戶的蠻夷自然可以歸入戶部管轄,但是那些羁縻州與不向國家納稅服役的蠻夷,卻隻能歸入朝貢體系之内,其與藩屬不過是程度不同的區别而已。
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濱,莫非王臣這句話,從來都不是曆史的事實,但是這一點也不妨礙它深入人心,并由此為文化核心,形成了古老的朝貢體系。石越一方面沉迷于朝貢體系帶來的既得利益——它使得宋朝對南海地區的經營名正言順,在将高麗與南海諸國納入華夏圈之時更加順理成章——因為華夏文明掌握了整個地區的話語權,使得那些當事國都承認朝貢體系是天經地義的,在宋朝擁有足夠實力的時候,這種觀念帶來的優勢是不可想象的,因為它能從心理上解除敵人的武裝。但另一方面,石越卻清醒地知道,哪怕華夏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優勢,也不意味着其餘的文明便沒有自己的尊嚴。人類文明并非是一座山峰,而是由群山組成,每個稱得上文明程度的人類社會,都可以有自己的山峰存在。你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,但是在心理上,你永遠需要去正視你的競争對手,否則,哪怕是再強盛的文明,總有一天,也會在高傲中迷失、堕落,被别人超越而毫不自覺,到那時候,便難免要付出慘重的代價。
古老的朝貢體系,在這方面是有缺陷的。但是石越既想享受其帶來的好處,又試圖保持其完整性,在其之外生硬地另立一個系統,就不會是這麼容易的事情了。禮部的主客司,甚至連禮部尚書王珪都覺得極其别扭,而且在實際事務上,也造成了相當大的不便與職權重疊,其被裁撤,事實上反映了宋廷效率的提高與務實。所以,連石越也對此哭笑不得,不知道這件事究竟是好是壞。
除此之外,在宋朝各地,也發生了一些值得一提的事情。
在南方,熙甯十一年以前,廣南東路與廣南西路的稅收,其總和甚至都比不上荊湖南路一個大一點的州,而且因為運輸與市場的原因,海外貿易的交易點,海商人們往往也更願意選擇泉州與杭州等城市,而并非廣州。這件事情在熙甯十一年終于發生變化,廣州一州的商稅,在這一年正式超過潭州之全部稅收。在廣南東路的移民數量雖然有限,但是卻帶來了更先進的生産工具與生産方式,也使得廣南東路的農業有了一定程度的起色。前三司使曾布因此政績而受到朝廷的表彰,本來其高升指日可待,但是另一件事卻影響了這件大人的仕途——為了溝通與荊湖南路、江南西路的交通,增加廣州對商人的吸引力,這位曾大人與薛奕将軍、蔡确大人合謀,竟然從南海諸島至注辇國控制的小島上,擄掠了三千餘土人為勞工,用于修葺道路,溝通河道,其中有一半以上客死他鄉。這件事情被一位派往廣南東路辦案的監察禦史發覺,一本奏章,讓曾布與蔡确各降一級,薛奕削侯爵,成為熙甯十一年下半年震動天下的大案。宋廷因此也着手海外第一次人事調動,将狄谘調任廣州,曾布調任淩牙門,蔡确調任歸義城,而三地的監察虞侯、常駐淩牙門與歸義城的監察禦史,則是因為失職,全部罷職換上新人——這種程度的調動,既是考慮到南海地區在早期需要倚重熟悉情況的官員,又可防止了他們在某地經營過久,形成尾大不掉之勢。不過由此次調動,也知道了三地在宋廷心目中的地位:廣州最重,其次淩牙門,其次歸義城。
而在西北,熙甯十二年的春節,石越與劉庠正興高采烈看着地圖上的驿政網慢慢的延伸,眼見就要遍布陝西一路大部分地區,這絕對是讓人歡欣鼓舞的。
而更讓人高興的是,重修三白渠等水利工程,也進展得十分順利。不過,這種表象的背後,卻同樣有着殘酷的現實。石越将留在陝西路的衆多西夏俘虜分成了三部分,一部分下級軍官和勇武的戰士,被石越打散整編入宋朝的禁軍——按當時的慣例甚至可以獨立成軍,這些俘虜會毫猶豫的向昔日的袍澤揮刀——向朝廷獻俘的那一部分,就被皇帝編成了一個營的完整編制,派往河北。但為了謹慎,石越還是按自己的習慣,将這些人全部打散整編;一部分老幼與随軍工匠,石越将老幼着派往馬監,将工匠編入作坊;而最大一部分普通士兵,則成為了石越的免費勞力——當然,名義上不是免費的。這些人被告知,西夏拒絕了對等交換俘虜的建議,更不刑徒sodu會出錢贖買他們,他們已經不可能回到故鄉。
唯一的出路,就是在陝西路的道路與水利工程完成之後,他們可以按自己工作量的多少,在宋朝的南方得到一塊大小不等的免征賦稅五年的土地。
這些俘虜們對宋朝南方的土地并不感興趣,但是這不是他們感不感興趣的問題,因為他們沒有别的選擇。石越不過是為了避免禦史的彈劾,減少道義上的阻力,用南方的土地為此來披上一塊稍稍溫情的面紗而已。
陝西路的百姓為了戰争付出沉重的代價,他們得到戰争帶來的這一丁點好處自然是理所當然的。如果為了所謂的道義,讓這些戰俘編成吃白飯的軍隊,或者便宜各級官僚,成為他們的私傭,卻還要征發陝西的百姓來修路通渠,在石越看來,這毫無疑問是一種僞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