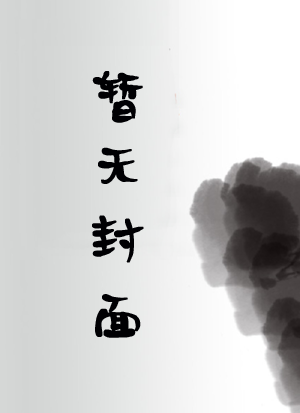我見章惇想走,心裡轉得幾轉,朗聲說道:“章大人且慢走……”一邊說着一邊慢慢走到章惇身邊,說道:“我并無怠慢之意,隻是這心裡卻是寒得很……”一副不勝感歎的樣子。
章惇見我相留,便停了下來,說道:“下官也不好多說什麼……總而言之,朝中有小人,石相多多小心就是了。”說完也不多說,便揚長而去。
雖然不知道他安的究竟是什麼心,但是做為我來說,還是有點感動的。不過從理智上來講,我還是清楚的明白,章惇此來,不過是給自己留一條路的。他似乎嗅到了什麼,而以他的才智,是不絕不願意把自己的前途全部壓在王安石身上的。但是他和蔡京又不同,他是新黨中的人,如果此時明顯的投靠過來,肯定要為人所不恥的。所以來點醒我一下,對他來說,應當是恰到好處之舉。
……
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寫了幾封書信差人送給李一俠和段子介,然後便寫了一個謝罪的折子遞了上去,連續三天步不出莊園一步。秦觀等人聽到風聲來找我,我也不接待,隻讓人在外面給他們各買了宅子……
這三天,消息不斷的傳來,先是說那些彈劾的折子被皇帝留中不發;然後就是幾個禦史在朝堂上公開彈劾,不依不撓;然後就是一些舊黨和中立的大臣幫我辯論,連地方上的一些地方官也寫奏章來幫我說話,雙方幾乎是吵得不可開交;而最讓人奇怪的,倒是新黨,據說王安石幫我說了幾句好話,而新黨的骨幹人物幾乎全部都默不作聲,隻有呂惠卿一個人帶着一幹小臣幫着那些禦史在那裡彈劾我,還有幾個頑固無比的極端守舊派,對我的攻擊比新黨還要狠些。不過總的來說,唱主角的還是那些禦史。
接下來的幾天,就是皇帝不停的召見執政大臣和元老大臣,詢問意見……風聲傳到太學和學院,有人想聯名保奏我,被秦觀等人給勸散了。一時間因為對我的彈劾,朝局一下子亂得一塌糊塗。而我卻隻在家裡聽戲唱歌,不問世事,當然消息卻是無論大小好壞,都能傳進府中的。
皇帝本來覺得這是挺小的事情,不過是幾個禦史彈劾我,卻不料得我在朝野中有如此巨大的聲望,如何處置這件事情,反而變得比較棘手了。一方面是禦史台的幾個禦史、禦史裡行,知谏院的谏官,再加上呂惠卿和一些官員;一方面是之前反對新法不讨他喜歡的一些勳舊大臣;而他最信任的王安石一反常态的和這些他不喜歡的人站在一邊,他的立場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中立偏向于我的。因為身為宰相,皇帝相問,他不能不答,所以他一方面說“彈劾的内容是無知小兒之見”,一方面又說我“非官非民,名不正言不順,殊不合禮制”,又說我“是宰相之器,然未任地方,終不能大用,而皇上恩寵太過,所以招人嫉妒”。這個老狐狸的意思我明白得很,就是想我把趕出京師,委我以地方大任,讓我在地方呆上三五年,别在皇帝身邊阻礙他頒行新法。三五年之後,法令已行,生米成熟飯,我就算入政事堂,也沒什麼辦法翻案,他對自己的新法的效果是很有自信的。他采取這樣的态度,也是明白皇帝并不是懷疑我,反而是想保全,而把我派到地方做幾年郡守,積點地方行政的經驗,皇帝也不是不動心的。
而我卻隻能一方面在家裡暗罵王安石這隻老狐狸,一方面就不斷的拜表,讓皇帝給我懲罰,以平息這場争議,擺出一副以大局為重的樣子。我不斷的做出謙退的樣子,告訴皇帝“不宜以言罪人,禦史們無論說得對不對,都不應當受到懲罰,以免阻塞言路”;一方面又對這麼多人幫我辯解“深感不安”;同時又自請懲罰,希望皇帝停止我的所有官職,并說自己決不願意做官……隻是皇帝看重,所以“不敢自棄”,不顧自己才疏德薄,在皇帝身邊參贊機務,補阙拾遺。言外之意就是我絕不願意出任地方官,你讓我到地方去,我就辭官不做,我在你皇帝身邊做官,還是因為看你皇帝對我君臣知遇之恩,我可不在乎什麼官祿前程的。
這一片混亂的局面遠遠超出了王雱的預計,他絕對沒有想到自己的陰謀會引發朝堂上各種政治勢力的直接對抗,他根本不明白我的存在雖然讓新黨很不爽,但是實際上卻是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,正是因為我的作用,使得舊黨們不那麼激烈——現在的舊黨,因為我的存在,根本不是王安石可以用斷然的手段解決的舊黨了。此時他把目标直接指向維持着朝局平衡的我,怎麼可能不引起混亂呢?
但是新黨的王安石派,卻出乎意料的在這場混亂中保持了穩重,并且似乎完全站在于風浪之外。這和王安石對我的政策是分不開的,他似乎認為隻要我把趕出朝廷就夠了,趕盡殺絕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現實;而一向對王安石言聽計從,似乎是王安石的哈巴狗的呂惠卿,卻一反常态的偏離了王安石的路線,而王安石卻似乎并不生氣——這是這場亂局中我所看不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