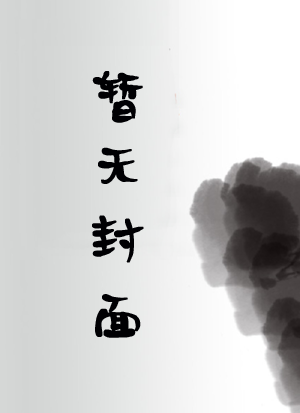“有欠謹慎!”——戶部尚書司馬光的額頭上,幾乎就差直接刻上這四個大字了。
“若是行,日後想要多少錢就可以印多少錢……”尚書右仆射呂惠卿心中的想法,也不經意地從嘴角的笑容中流露出來。
而餘下的宰輔們,有幾位被這前所未有的大膽計劃所震撼,腦海中短暫性出現空白的現象;其他尚屬清醒的大臣,則在心中反複衡量着韓維提出來的計劃的利弊——包括對大宋朝的利弊,也包括對自己利益可能産生的影響,一時之間,竟然難以下出判斷。
韓維提出來的計劃,表面上真的是充滿了誘惑力。
但是抛開派系之間的立場不提,政事堂中許多大臣,還是從這種誘惑當中,直覺的感受到了危險,雖然他們并不清楚究竟會有何危險。
“旁門左道!”司馬光心中十分地排斥行交鈔這種危險的想法。他始終相信,真正理财的王道,就是朝廷的君臣厲行節儉,輕徭薄賦,使百姓們種好地,生産出足夠的糧食,這樣國家自然會上下富足。其他所有的理财方法,在本質上,都是屬于歪門邪道——“天下的錢财有限,不在官便在民,官多自然民少!”雖然司馬光并不懂得什麼叫做“零和遊戲”,然而他卻固執的保持着這樣的信念:其他所謂的“理财之術”,都不過是“零和遊戲”而已。
而呂惠卿猶疑的,則是提出這個計劃的人——韓維是衆所周知的“石黨”!他的計劃便是脫胎于石越的構想,他有必要替風頭正健的石越再添新功嗎?石越與高遵裕在陝西取得勝利讓朝野為之振奮,一時間譽聲如潮,但是真正要為補給、财政操心的,卻是他呂惠卿!呂惠卿心中頗覺憤憤不平。
當然,他自動忽略了司馬光等人的工作。
呂惠卿望了各懷心事的政事堂宰輔們一眼,似乎感覺過于長久的沉默并非解決問題的辦法,便輕輕咳了一聲,說道:“諸位大人以為此策如何?”
“某以為不妥!”司馬光絲毫不留情面地說道,“無論金、銀、銅、鈔,皆為無用之物。于世間有用之物,乃是糧食與絹布。天下農夫每歲所耕之地不變,則所産之糧不增多;天下農婦所種之桑麻棉不變,則所織之布不增多。而朝廷卻要行所謂‘交鈔’,此是以此無用之物,奪天下農夫農婦所産之糧布,與加稅又有何異?”
戶部尚書所說的,是一種樸素的經濟道理,立時赢得在座大部分人的認同。
但是太府寺卿顯然也有他的道理,韓維立時向司馬光欠身說道:“非也!某以為,司馬公所言,隻見其一,不見其二。”
“願聞其詳。”說話的是尚書右仆射呂惠卿。雖然韓維與石越本質上都是他的政敵,但相比而言,他更願意見到有人讓司馬光難堪。
自從司馬光入朝之後,呂惠卿與司馬光之間在皇帝面前公開的互相攻讦,就過三十次;至于在政事堂的互相批評,更是家常便飯。然而奇怪的是,雖然呂惠卿曾經數次用計,試圖激怒司馬光,逼性情剛強的司馬光主動請辭,但是司馬光卻似乎頗覺其意,哪怕在政事堂争得面紅耳赤,卻絕不肯辭職。呂惠卿自然不知道司馬光有多重的原因,不敢輕易言退方面,因為受到太皇太後的重托,讓忠君觀念極強的司馬光有了一種肩負重任的感覺;另一方面,卻是因為當年王安石雖然與司馬光政見不合,但是司馬光潛意識中,對王安石還有一種信任,懷着一種僥幸認為王安石也未必不能成功,但是對呂惠卿,司馬光卻是認定了他不過是一個奸佞小人,司馬光自認為如果自己離開朝廷,将會成為國家的罪人,因此雖然屈居呂惠卿之下、哪怕與呂惠卿争得怒沖冠,司馬光始終不敢放棄自己的責任。
但是司馬光的這些心理,卻是呂惠卿所不能理解的。所以呂惠卿始終希望借用一切機會,來拔掉政事堂的這根眼中釘。
韓維并不知道自己此時已經成為呂惠卿打擊司馬光的工具,他注視司馬光,朗聲說道:“司馬公當知慶曆間事,慶曆之時,江淮之地便有錢荒,其因便是朝廷需調集銅錢應付西夏元昊之邊患。直至熙甯以來,東南錢荒,依然如故。熙甯二年呂相公便曾建議坐倉收購軍兵饷糧,而令東南漕運糧改納現錢,當年司馬公曾上章論之,以為如此則會加劇東南錢荒……”他這句話說出來,政事堂中呂惠卿與司馬光都表情尴尬,馮京、吳充等人卻面露笑容。韓維沒有覺察到自己失言,兀自繼續說道:“此後朝臣論東南錢荒者甚衆,直至熙甯九年夏,張方平相公亦曾言東南六路錢荒,道‘公私上下,并苦乏錢,百貨不通,萬商束手。’且言‘人情日急’。是故石越為杭州守牧,便曾上章論之,請朝廷于秋收之時,許農夫納米不納錢,以免使農人同時賣米,加劇米賤錢貴,重傷農夫。後其入朝,又數論之,天子恩德,于熙甯九年秋頒诏許之,天下稱頌之聲,今日尤不絕于道。然則東南錢荒,卻并未完全解除。”
韓維說到此處,連司馬光都暗暗點起頭來,因為韓維提及的,實是宋朝經濟領域面臨的一個死結!大宋君臣,對此都束手無策。果然,便聽韓維繼續說道:“天下錢事,一面是東南錢荒,緻使米賤傷農,百貨不通,萬商束手;一面卻是銅貴錢賤,銅禁未開之時,天下銷錢鑄銅器者已不可勝數,自王介甫相公開銅禁後,更是風行天下。蓋銷镕十錢,得精銅一兩,造作器物,即可獲利五倍甚至十倍,天下誰不願為?遂使錢荒愈重。石越論及此事,以為以銅鑄錢與以銅鑄器,利潤相差如此,是銅錢之值賤也!若依常理,則既有錢荒,則當錢貴,錢貴則鑄錢監當有重利,而今日之事實,卻是各地鑄錢監,因銅價貴于錢價,若能不虧,已是萬幸。”
韓維說的,的确是當時的怪現象,一方面東南錢荒,流通市場缺少銅錢,導緻錢貴米賤,傷害農業;另一方面,卻是銅錢的市場價值低于它的實際價值,導緻官府鑄銅錢不能獲利甚至是虧本,而同時,卻有大量的銅錢被鑄成銅器,以及流出海外——因為宋錢在海外的購買力,數倍于它在本國的購買力!由此更加劇了錢荒的現象。
這是宋朝人難以解釋的現象,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當中。他們鑄造的銅錢,既是貴的,又是便宜的!哪怕就在缺少銅錢的東南諸路,也是如此,那裡的銅錢一方面缺少,一方面卻除了傷害到米價之外,并沒有導緻物價暴跌,甚至是米價,也處于一個相當的水準,所以使得銅錢不斷的外流——曾經有來自倭國的商船,一夜之間将一座城市的銅錢全部買走!也有非法的海商,載着滿船滿船的銅錢出海,去海外購買過這些銅錢在大宋境内的價格一百倍的貨物!
這也許可以解釋成宋朝政府在平準物價方面做得多麼出色——哪怕是虧本,也在不斷的鑄造銅錢,使得東南地區雖然看起來永遠都在缺錢,但是至少不是不斷的缺錢,流入量抵銷流出量,從而維持了一種相對的平衡;也可以解釋成因為宋朝的經濟水準遠高于她的鄰國,所以宋朝的物價哪怕在缺少銅錢的狀況下,依然遠高于她的鄰國。
但無論如何,對于宋朝來說,這始終是個難題。連石越都無法解釋清楚這種現象,更不用說設法解決了。雖然這隻是一種局部現象,但是對大宋東南地區的工商業,卻有十分大的影響。因為錢荒,導緻東南地區的市場被限制在一定的規模之内,無法擴大;又因為錢在大宋境内價賤,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唯有以物易物,才能得到最大的利潤——從海外運回銅錢,那是傻子才做的事情,因為哪怕是将銅錢運回來鑄成銅器,在算上運輸費用之後,其利潤相比海外貿易的利潤,也是微不足道的,所以每個商人,都務求将手裡的每一文銅錢都換成貨物運回大宋。但是東南諸路的市場規模,卻無法吸納這過多的貨物,大部分的貨物,隻能運往汴京。一旦汴京也吸納不了時,與其降價賣到其他地區,商人們更願意削減貿易的規模來保證利潤。
于是大宋東南地區的展,就這樣被限制了。
整件事情雖然引起了宋朝精英的普遍關注,但是在當時的人們而言,是很難從更深的層次來理解這個問題的。但盡管如此,韓維還是憑借着自己粗淺的理解,以及在太府寺卿任上所得到經驗,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法。雖然他的認識并不深刻,考慮的問題也并不周全,但實際上卻很可能是有效的。
所謂的“瞎貓撞上死耗子”這種事,有時候也是存在的。
這位太府寺卿在政事堂上繼續着他的慷慨陳詞:“所以,某以為,目前便有一劑良方,可以解決東南錢荒與鑄錢虧損的問題!”
他說到此時,衆人都已漸漸明白他的理由。
“某以為,在東南諸路行二百萬貫的交鈔,便可以有效的解決東南錢荒,交鈔不懼外流,不懼銷鑄,隻要将最新出現的彩色套印技術收歸官有,控制住幾家最好的造紙坊,那麼盜印的問題,也可以抑制在相當小的範圍内。而且相比銅錢而言,交鈔攜帶也更為方便。此外,朝廷還可以在川陝行一百萬貫的交鈔,其目的一方面是為陝西路興修水利提供資金;另一方面,則可以在川陝地區,遂步回收鐵錢,停止鐵錢監鑄鐵錢導緻的虧損。川陝停用鐵錢,尚有一個意外的好處,便是可以使墨吏在收稅之時,少了用鐵錢與銅錢之間的兌率來剝刻百姓的機會,于川陝百姓而言,無疑亦是一大德政。因此,某以為,川陝的交鈔,甚至可以行更小面額的!”
吏部尚書馮京聽到韓維興緻勃勃的說完,不由試探着問道:“一旦東南六路與川陝諸路行成功,交鈔是否要推行天下?”他問出了所有人的心聲。
“自然要推行天下!”韓維毫不遲疑的說道,“交鈔相比銅錢與鐵錢,方便而不費。銅礦産量始終有限,諸君皆知日後朝廷尚有一個地方需要大量用銅,若是找不到取代之物,隻恐錢荒越來越嚴重!”衆人都知道他說的自然是火炮,當下盡皆默然。
隻有司馬光依然搖頭,道:“以紙為錢,與布為錢,又有何區别?隻恐重蹈王莽覆轍。”
“司馬公此言差矣!”韓維聽到司馬光拿他與王莽相比,臉色不由沉了下來,高聲辯道:“交鈔隻需有銅錢為本,可以用來交稅,且能抑制盜印,百姓自然信任樂用。豈能言與王莽同?”
“隻恐公用意雖佳,終敗國事!”無論韓維說得交鈔如何有百利而無一弊,司馬光始終相信天下沒有這般輕易的事情。隻不過,他心中雖然有強烈的不安,但是卻怎麼也想不出來究竟是為什麼,隻是隐隐感覺這後面,存在着一個巨大的隐患。
“司馬公若以為不妥,當說出道理,在座皆是朝中大臣,非三歲小兒,豈可危言聳聽?”呂惠卿在一旁用譏諷的口氣說道。
司馬光霍然起身,瞪視呂惠卿、韓維。韓維心中終不願與司馬光為敵,便将目光避開;呂惠卿卻是若無其事的迎視司馬光,眼中盡是嘲谑之意。司馬光強按心中怒火,指着呂惠卿、韓維,罵道:“他日壞國事者,必爾二人也!”
他的這句話,卻未免太過份了。韓維騰地站起,正要反唇相譏,卻見馮京向自己使了個眼色,他心中立時想起以前石越和自己說過的話來:“司馬君實性格剛直、嫉惡如仇,日後在朝中若有沖突,持國當相忍為國!”他暗暗吸了一口氣,強按捺住心中的怒火,向馮京點點頭,慢慢坐回位置上。
政事堂終于沒能就行交鈔的問題達成一緻。不僅僅是司馬光堅決反對,連馮京、吳充、王珪等人都顧慮良多,雖然韓維說的頭頭是道,但是畢竟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嘗試,沒有人願意承擔失敗的責任,也沒有人承擔得起失敗的責任。
然而大宋的财政困難卻并不會因為政事堂達不成一緻而稍有遲緩。
既便是呂惠卿,都感覺到了府庫的捉襟見肘。
若是再想不出來好的辦法,便隻餘下設法加稅一條路了。
政事堂在七天之内,就大宋的财政困難與行交鈔的問題讨論了四次。韓維對交鈔的行方案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完善,行的數量也由東南諸路的二百萬貫修改為一百二十萬貫,川陝的一百萬貫降為八十萬貫,但是政事堂諸相卻始終無法達成一緻。
政事堂中惟一流露出支持意向的,出乎韓維的意料,竟然是呂惠卿!
時間就這樣不知不覺地從政事堂的大門外溜走。
半個月後,陝西路安撫使司。
“陝西一路,自仁宗朝以來,百姓賦稅實際三倍于他路!”陝西路轉運使劉庠向石越着牢騷,“各地繳納兩稅,都在本州本縣,惟有陝西一路,朝廷為了節省官府運輸開支,命令百姓支移,結果陝西各地的百姓居然要千裡迢迢去延州、保安軍等處交納兩稅,否則便要交納‘道裡腳錢’!什麼‘道裡腳錢’!簡直是毫無‘道理’!”
“運使大人所言皆是實情。”接着劉庠的話的,是安撫使司參議豐稷,“自六月一日開征夏稅以來,百姓便開始轉運于道,辛苦不堪,見者無不為之歎息。”
“朝廷久久不批準本路實行驿政改革,本府亦無可奈何。本府昨日已經上表,請求朝廷準許,陝西路支移,上等戶不過三百裡,中等戶不過二百裡,下等戶不過一百裡。希望政事堂諸公能夠體察民情……”石越隻能苦笑搖頭,宋朝夏稅自六月一日起征,分為三限,每限一個月,至八月底結束。而陝西路百姓最為困苦,相比在本州本縣交納兩稅,他們的實際交稅額,是翻了整整五倍。如果能順利推行驿政馬車制度,再加石越的折衷措施,那麼陝西百姓的賦稅負擔,至少可以降低三倍!既便是石越的請求不被批準,隻要驿政馬車制度完善,百姓們省下的運輸費用,也會相當的可觀。
“與其空等政事堂諸公決策,不若吾輩先行動手!”劉庠眼見面前有一個好辦法可以減輕百姓的困苦,卻因為必須等待汴京的批準而不能施行,心中早就十分不耐。
“劉大人所言甚是。”另一位心庠難耐的人——石越的幕僚陳良也忍不住附和道:“何不先試行開通一些地方的驿政馬車?于百姓之困苦,能減輕一分,便是一分。”
“下官亦以為可。”豐稷也用期盼的眼神望着石越。
石越心中亦怦然心動,不覺将目光移向李丁文,問道:“潛光兄以為如何?”
李丁文垂思忖半晌,忽然凝視劉庠,笑道:“劉大人為朝廷陝西路轉運使……”說到此處,突然停了下來,隻是望着劉庠微笑。
劉庠莫名其妙地望着李丁文,不知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。
“敢問大人,轉運使是管何事?”李丁文見劉庠不解,又問了一句。
“一路之民政、财政,以及轉運之事!”
“原來如此!”李丁文作出恍然大悟的樣子。
劉庠一怔,腦中突然靈光一閃,猛的明白過來,原來李丁他是轉運使,實可以在“轉運”的名義下,開始驿政馬車制度的建設,根本不必請示石越。他立時眉開眼笑,向石越說道:“子明,可否将府中的陳先生,借我一用?”石越卻是知道李丁文分明是拿劉庠當槍使,隻不過劉庠卻也是心甘情願當槍——他當年連王安石都不放在眼中,哪裡會理會一個呂惠卿?當下便笑着向陳良說道:“又要勞煩子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