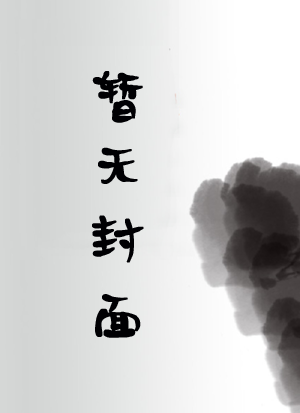“役法……”
“正是。”劉庠放下茶杯,侃侃言道:“本朝之最大症結,就在役法。”一面注目範純粹,道:“德孺可為子明略言唐以來役法之變。”
“是。”範純粹微微點頭,溫聲說道:“唐初行所謂租庸調之制。租為田稅;調為絹、綿、布、麻之稅;此外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,不服役者,則納絹布替代,是為庸;若政府額外加役,加十五天,則免調;加三十天,則租調全免。每年額外加役,最多不得過三十天。若有雜徭,亦不得過三十九天,若過,則要折免其他賦役。此唐之所以富強也。至武則天、唐玄宗,均田之法漸壞,租庸調亦漸漸名存實亡,又出現所謂地稅與戶稅,此兩稅法之先聲,戶稅實為人頭稅,按戶收稅;地稅則為田稅。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,楊炎終于制定兩稅法,兩稅法之要義,是‘量出以制入’,朝廷根據财政支出定出總稅額,分攤州縣;又按丁壯與财産訂戶等,依戶等納錢,依田畝納米粟。夏秋兩季征稅。租庸調、雜徭、各種雜稅一律取消。本朝之所以不抑兼并,實與兩稅法有關。因為國家稅收之主要來源,完全不需要抑制兼并。此亦本朝立國與唐初立國之異。然而若依兩稅法之精神,那麼百姓在交納兩稅之後,是不需要再服任何徭役的!”
範純粹所說之事,石越自然清清楚楚,但是自範純粹口中說來,卻依然讓人聞之歎息。便聽範純粹又說道:“本朝承五代之弊而不能改,兩稅之外,又有丁口之賦與雜變之賦,要随同兩稅輸納。且丁口之賦不論主戶、客戶,一體交納,兩稅之外,再征了一次人頭稅。百姓之負擔,較之兩稅法,已經變重。特别無地之民,更深受其害。最為不堪者,卻是交了兩稅與丁口之賦、雜變之賦以外,還要服差役!”
“本朝差役,有主管運送官物或看管府庫糧倉的衙前,有掌管督催賦稅的裡正、戶長、鄉書手,有供州縣衙門随時驅使的承符、人力、手力、散從官,有逐捕盜賊的耆長、弓手、壯丁等等。王介甫欲行免役法,其免役錢可比唐之庸,然而征庸之後,差役往往并不能免。是役法之禍更烈。本朝若真欲寬政為民,依區區之意,是應當盡廢丁口之賦與雜變之賦,更應當讓百姓一體免役,使兩稅之外無役稅,此方是為百姓着想。但是本朝立都汴京,冗兵冗官,國庫空虛,想要輕徭薄賦,畢竟也隻能是空想。”
聽到這裡,劉庠接過話來,道:“陝西一路,百姓所受刻剝,實為國朝之最。尤其是役法,因為與西夏曆年交兵,百姓被征轉運糧草,組織鄉兵弓手,别外百姓還可輪息,陝西百姓卻幾乎無一日安息。興水利,淤河為田,皆是大工程,全靠财政雇人進行,根本不可能做到。而若要征百姓,百姓已經疲于奔命,實不堪再被驅使。我輩一心為民謀利,又豈能不顧事實,反而害苦這一路百姓?故此陝西路所難者,實是無錢可用,無人可使!”
石越望着映在窗紙上的燭光,沉吟良久,忽然試探性的問道:“解散一部分鄉兵弓手如何?”
範純粹搖了搖頭,苦笑道:“那是朝廷的敕令。事關軍國邊防,我三人都承擔不起。”
“沿邊或者還需要弓手協助守衛,與西夏不接壤諸州縣,要弓手何為?”
“怕的是萬一。而且此事亦非陝西官員可以決定。”
三人再次陷入沉默當中。石越苦思良久,實無半點良策。須知正如劉庠所言,興水利、淤河為田,充足的财力之外,更需要組織大量的人力。但是陝西一路,早就變成了一個邊防組織,百姓們在承擔了沉重的賦稅之外,還要被征來替軍隊轉運糧草軍需,修築城池要寨,還要組織民兵,來保衛自己的家園。在這樣的地區,要辦大工程,隻有兩個辦法:一是不顧百姓死活,強行征,以蠻橫家長式的作風,為了“百姓的利益”反而去置百姓于水深火熱當中;另一個,則是從邊防機器中來抽調人手搞建設,但是這種可能危及到國家安全的行為,會不會被朝廷認可,會遇到多大的阻力,是可想而知的。先,石越就可以确信,政事堂呂仆射,就一定會用國家安全的大義,來竭力阻止。
“先用一年的時間去準備。”石越忽然開口說道:“希道兄、德孺兄,為官一任,造福一方。此事不可不為,亦不可操之過急。在半年的時間内,希道兄要将陝西路需要興建、修複的水利設施與淤河計劃按輕重緩急列出清單來,包括估計要投入的人力與财力以及時間,屆時可能得到的收益,同時可以進行一些較小的計劃,了解實際的困難。而我用這一年的時間,來想辦法解決人與錢的問題。”
劉庠與範純粹對望一眼,有點懷疑的說道:“我估計要組織的人力,最少要數十萬;花費的錢财,絕不會低于數百萬貫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石越擺了擺手,道:“所以我們分工合作。兄等去巡視地方,做好準備的工作;而我來想辦法,去把東風借來。”說罷,他注視着劉庠與範純粹,鄭重的說道:“希望希道兄與德孺兄不要以為我是戲言。”
“不敢。”
“治理地方,須要寬猛相濟。以往陝西路百姓被驅使過度,我輩來此,定要殚心竭智,使百姓稍得休息。在大修水利之前,凡行政之事,能寬得百姓一分,便是百姓得一分利。切勿以善小而不為。地方不相幹的雜徭,一定要約束各州縣守令,越少越好。凡做一工程,事稱須得先想好投入與收獲是否相得,利倍于害,方可為之。若是勞而無功,更困百姓。”
“正當如此。”劉庠點頭道,“惟陝西之大治,終須要西北平靜。”
石越微微歎了口氣,西夏不平,西北如何能平靜?豈非緣木求魚?他轉過頭,注目範純粹,換過話題,說道:“校情況如何?”
“登記之小學校有八百餘所,諸縣多者有十數所,少數不過一二所,規模大者數百人,小者二三十人。各州皆有州學,大小不一。此外尚有橫渠書院與京兆學院兩學院。在京兆府與河中府,各有一所數百人的技術學校。惟本路僅有一座官立圖書館,即京兆府官立圖書館,藏書不過三萬卷。連河中府都不曾有圖書館。下官打算一方面派人去國子監遊說,希望争取國子監能夠盡早将陝西路列入計劃中;另一方面,則希望能從地方募資,建立民立圖書館。陝西畢竟太窮,有許多書生走半個月甚至一個月的路到京兆府官立圖書館看書,實在可歎。”
石越靜靜聽範純粹說完,方悠悠說道:“德孺不可以被數字所誤。國子監現階段重視的圖書館與州縣學院,固然重要。但是德孺眼下不如先調查一下那八百所小學校,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。如果不能開設國子監要求開設的課程,保證合格的師資與教學條件,是不能夠享受抵稅待遇的。要防着奸民從中鑽空子,朝廷白白流失賦稅。”
範純粹怔道:“難道有人空設學校,卻不辦學?”
“德孺一查便知。有人用私塾義學來充小學校,有人設了學校的名義空占稅賦,國子監的檔案上有這個學校,但是去當地找,卻根本找不到。對于奸吏來說,辦了學校既是政績,又可以從中間以抵稅的名義侵占大筆賦稅,國子監遠在京師,核查困難無比;而僅僅是公文上的登記,地方民衆則根本不知道,想舉報也不可能。離任之前,能擺明下任就一起狼狽為奸;若是擺不平,則可以上報撤銷學校……”
石越兀自侃侃而言,範純粹的臉早已沉了下來,一臉怒容的罵道:“豈有此理!明日起,我便逐一調查這八百餘所小學校,看看究竟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!”
※※※
渭州城。王韶回京後,原熙河地區的軍事歸李憲總管,而秦鳳以至環慶一帶諸州軍的軍隊,則由渭州經略使高遵裕節制。按照新官制,渭州經略使并不是正式的官職,而隻是臨時的差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