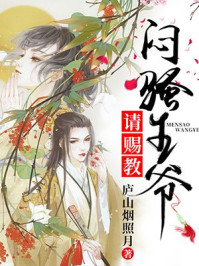聽得一愣愣的相芙,微微偏頭不解地看向顔娧。
能不能給她說明一下,什麼叫做“偏向純良?”
她對純良這字面是不是有什麼理解錯誤的地兒?
雖然她不常将五彩斑斓的雙手放在外頭招人,一個來自南楚擅長玩弄毒物的弄蠱人怎麼也搭不上邊啊!
心中雖紊亂神傷,深知時間不夠充裕,相芙再擡眼也撇去了那些無謂的難堪,沉着問道:“為何信我?”
“妳是最不希望相澤殒命之人。”
她的決絕說服了泰半不安懷疑,顔娧深幽眼眸裡透着淡淡賞識,也不再隐瞞她的考慮,坦然說道,
“他能不仁,妳卻無法不義,愛多了終究是輸家,想不想他活命,同妳想不想攆死蝼蟻般了。”
顔娧提氣以風刃準确切斷取魂針長度,針尖小心翼翼收進懷中後,便将半截針末深埋相芙發髻裡,看似深深紮入腦殼裡。
相芙聽得又是眼眶一熱,句句真實又字字剜心,梗在兇臆裡的疼痛彌漫了周身,三千青絲裡的疼痛如何比拟?
終究是輸家的認知,叫她回避清澈眸光,狠狠咬着銀牙,終究沒讓感性淹沒理性,深深吸了口氣緩緩說道:“不離島即可?”
顔娧眸光清冷回望門外由遠而近的腳步聲,負手于後,從容淡定地走向支摘花窗旁,沉着說道:“待他痊愈之日自然可以離島。”
“等等。”喊住已在窗外的纖瘦身影,相芙憂心不已地提醒道,“我不清楚表哥說的醉夜歸是何物,請妳善加珍重。”
若有所思的清冷眸光裡沾了抹審視的味道,顔娧唇線微勾。
“知道了。”
待确定顔娧離開了宅子,她枕回該有的位置,閉上雙眼不動聲色地調整初初恢複内息。
渾身裹着神秘的小丫頭竟真解了相家之難,面上在怎麼清冷寡淡,不願承認期間有何幹系,心照不宣她還知道怎麼做。
雨田城被莫名踐踏的無辜少女們,慢了一步的心疼撻伐着她已有數年,如若容家早些出現,是否能拯救?
相芙自嘲的一笑,于她實事求是的性子,從不考慮假設性的問題。
問題既已發生,如何解決才是唯一需要納入思維之事。
門扉被輕緩推開,稍稍恢複氣力的相澤被攙扶來到床沿,揮去侍婢徑自落坐床畔。
冷得有如冬日冰雨般的纖長指節滑過榻上失了皿色的蒼白面容,清冷虛弱的低沈嗓音透着惋惜。
“怎麼不相信表哥呢?”
“待表哥先拿下相家不好?”
“有相家作為後盾,拿回北雍屬于我的一切有何難?”
在炎夏夜裡聽着這些話語,相芙格外心寒,冷得情願從沒聽過。
原來祖母用心看顧了大半輩子的表哥,心心念念的竟是要拿下相家?
“表哥定會好好待妳的。”
卸下衣物發出的窸窣聲響,明知做戲仍使得榻上的相芙寒毛直豎,小姑娘用意竟在此?怕她後悔死心踏地從了相澤不成?
聽清私心,明白用意,叫她能下定決心守護相家?
豐沛内息充塞着周身大穴,原先閉塞無法再進的氣脈被沖破,感知比平常好上數倍不止,因此閉眼洞悉相澤的行動着實不好過,明知他無力為之,仍糟心得極力克制将人推下床的沖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