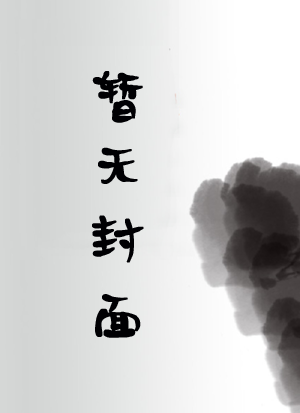馬車跑得一陣,我吩咐石福把速度放慢下來,緩緩而行,我掀開窗簾觀賞外面的風景。從道邊的疏林中,隐隐能看見幾間茅舍,遠處的草橋靜靜的躺在細細的流水之上,幾葉扁舟泊在河邊的老樹下之下,又有幾個腳夫趕着一車煤球向汴京城走去……
這種畫中風情,讓人陶醉。倘不是因身處國家權力之旁,倘不是因為早已預知這個社會可能會走向的結局,單看這景象,誰忍心去打破這詩意般的甯靜?但是帝國的喧嚣聲漸漸入耳,這個注定是大改革的時代,是不能再允許社會如此平靜下去了。
仿佛是為了證明我的感歎,身邊漸漸傳出來喧嘩的聲音,路上行人愈來愈多,有人騎着毛驢悠閑的漫步,有人坐在轎子上享受有錢人的特權,也有人歡聲笑語,也有人愁眉不展,騎馬的,挑擔的,人們的方向隻有一個,那就是汴京城。
一個小厮興奮的指着遠處依稀可見的一些建築,對我說:“老爺,你看,那是咱家的印書坊……”我微笑着回應他,眼光所及,卻發現一個騎在驢背的書生正拿着一本新書在讀。
我對這個社會的影響,也許沒有我想的那麼大,但是總有一些如細細的毛毛雨,無聲無息的沁入這片土地吧?
不知不覺之間,馬車已經入城,汴河上糧船雲集,船隻往來,首尾相接,或由纖夫牽拉,或是船夫搖橹,有的滿載貨物,逆流而上,有的靠岸停泊,緊張地卸貨。名為虹橋的大木拱橋上,人們熙熙攘攘,一路行去,就進入了城樓以内的街道,可以看見兩邊屋宇鱗次栉比,有茶坊、酒肆、腳店、肉鋪、書店、廟宇、公廨……商店中有绫羅綢緞、珠寶香料、香火紙馬……又有醫藥門診、大車修理、看相算命、修面整容,各行各業,應有盡有。大一點的商店門樓紮着“彩樓歡門”,懸挂市招旗幟,招攬生意,街市行人,摩肩接踵,川流不息,有做生意的商賈,有看街景的士紳,有騎馬的官吏,有叫賣的小販。有乘座轎子的大家眷屬,有身負背簍的行腳僧人,有問路的外鄉遊客,有聽說書的街巷小兒,有酒樓中狂飲的豪門子弟,有城邊行乞的殘疾老人,男女老幼,士農工商,三教九流,無所不備。
回想起初到這個世界的情景,暗暗裡也感歎着人生的際遇……
我讓石福把馬車停到汴河邊的一座酒樓旁,下得車來,擡眼望去,隻見市招上三個大字:“群英會”。我嘿聲失笑,快步走了進去,兩個厮連忙緊緊跟上。
早有酒保上來招呼着,我信步上樓,要了幾碟小菜,一壺熱酒,淺斟獨飲,兩個小厮卻讓他們另外叫了酒菜在旁桌吃着。
這個酒樓位置卻是極好,臨窗往去,正可見汴河景緻,河的那一頭隻有稀稀的建築隐在樹林當中,于鬧市中見雅靜,頗具情調。
當我對窗淺斟,自得其樂之時,幾個年輕人争辯的聲音突然傳來,循聲望去,是在酒樓的另一側靠窗處,幾個戴着方巾,儒生打扮的年輕人在大聲争論着什麼……我傾耳聽來,卻依稀隻聽得幾句“青苗……鋼鐵……邊事”,原來是在議論時政。
我正微微搖頭,把自己的心緒從那邊收過來,卻聽到一陣腳步聲,一個葛衣老頭帶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兒上得樓來,看那打扮,不是說書的就是賣唱的,自到宋朝以來,從未有暇聽過這些民間的曲藝,不料今日有此眼福,我不禁好奇的轉向這爺孫倆。
卻聽那老人告了個罪,說過幾句場面話,聽得明白了,竟是說評書,那老頭說幾句書,那女孩兒或唱幾聲,或拉個小曲兒……說的故事卻是當朝石相公的。
我正納悶着呢,什麼“石相公”呀?我怎麼不認識呀?細細聽了幾句,那卻是我的一些事情,不禁嘿然失笑。原來不知有哪個好事的書生把我落難寺中,虹橋吟詩,做煤爐印書籍,受天子恩诏,開書院寫新書等等故事編成評書給這些藝人來講,想我突然崛起,從出名到身居高位受皇帝重視不過忽忽數年,的确會有不少百姓對我的事情感到好奇,這評書說起來也不是沒有市場……
隻是難為這寫評書的把我的事情打聽得這般清楚,連我那兩個小厮都張大嘴巴聽着,一邊眨巴眨巴着眼睛望着我,有點難以置信的樣子。
我本來不以為意,倘在現代,做這樣的炒作我也蠻喜歡,那評書說得對我也無甚惡意,我聽到那青苗諸法,寫的人也多方宣揚我的功勞……隻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,竟然多了一種小心謹慎的毛病,我想到這評書倘若被朝中痛恨我的人聽到,參我一本,倒也是個大麻煩,但是便我知道人家要借此參我,我也無可奈何,我能禁止這些人說嗎?呵呵……想到無奈處,我也隻好給自己勸上一杯了。